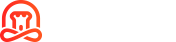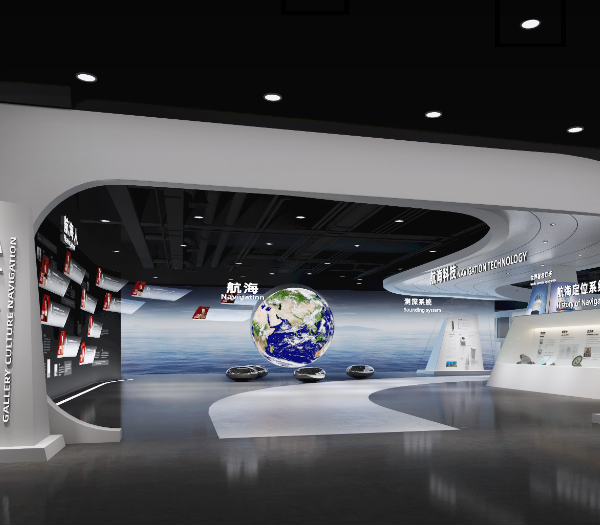- 项目名称:广州雅居乐·黄埔创新中心
- 设计总监:彭征
- 主案设计:林俊武,招婉莹
- 项目管理:林俊武,朱云锋
- 设计单位:广州共生形态工程设计有限公司
- 企业网站:www.cocopro.cn
- 项目业主:雅居乐地产
- 业主团队:魏星,左迪,吴敏华
- 项目地点:广东广州
- 设计时间:2019年02月
- 竣工时间:2019年12月
- 主要材料:仿石涂料,热转印木饰面,仿石铝单板,不锈钢,灰色大理石
- 建筑设计:广州宝贤华瀚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
光·见自己 在柏拉图手中,光是洞穴理论的逻辑主线,在笛卡尔手中,光是怀疑论的清晰回答,在设计师手中,光是空间的主角,有光才有空间。主角出场,重雅轻俗。重轻并非褒贬,而是度量,雅俗亦无高低,只是二元相对的概念。在此案中,雅若是七分克制,俗便是三分放纵。城市展厅内,三面高窗来光,若原样保留,光便散掉了,封去两面,把光攒簇于一处,空间的格调就出来了。
用厚重的墙体塑性光的形状,当光束自头顶洒落,一个奇妙的场域便形成了:幕墙厚重,步梯蜿蜒,圣光一束天外来,在这样的空间之中,聆听内心本真的声音,发现自我的价值与需求,平生出几分仪式感。此情此景,与其说空间是光的容器,倒不如说是光雕刻了空间。
燕·见天地
对于现代人而言,时间不过是钟表上的数字,而在钟表出现之前,时间藏匿于自然万物之中。日升月落,雁去燕来,都是时间的表征。设计师认为,只有将时间带入空间之中,才能把空间的秩序叠合于宇宙的秩序之中,形成一个富有诗意的系统。 “式燕且誉,好尔无射”“燕子家家入,杨花处处飞”,燕子作为时令鸟,与人类早期的生活、风俗息息相关,从先秦的图腾、神鸟到魏晋以后的自然鸟,再到现代的“燕子哲学”,小小的燕子走出了一条脉络分明的路。将燕子植入空间,可以说是对人类童年印象的捕捉,设计师试图以此唤起人们的集体记忆,还原人类与自然的关系,建立起新旧之间的对话。
巢·见众生
燕子将时间与记忆带入了空间之中,也让空间有了垂直的意义(天与地)的联系。因为有了燕子的动,才越见空间的静。太空旷静谧的空间,难免让人生出渺小之感。立墙隔断最简单,却非上上之策。 中国文人讲境界,分隔与不隔两种。隔,如雾里看花,不隔,如豁入耳目,前者过于委婉,后者失于直白。设计师的选择是:在空间的中心,筑起一个“巢体”,与建筑在形状上形成围合,以此消解空间的空旷感。在心观的层面,巢体是鸟类繁衍、孵化后代的容器,守护着生命最初的温暖,而这亦是见自己和见天地的终极意义。
设计师试图将自己的生命感悟外化到空间之中,从物理(光、燕、巢)与心理(三见)两个维度展开,为人们筹划出一个完整的体验过程,感知自己的存在,看见宇宙的辽阔,乃至看见众生的悲悯。都说设计载道,这岂非就是一次有意义的小尝试?
▽ 分析图
▽ 平面图
{{item.text_origin}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