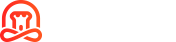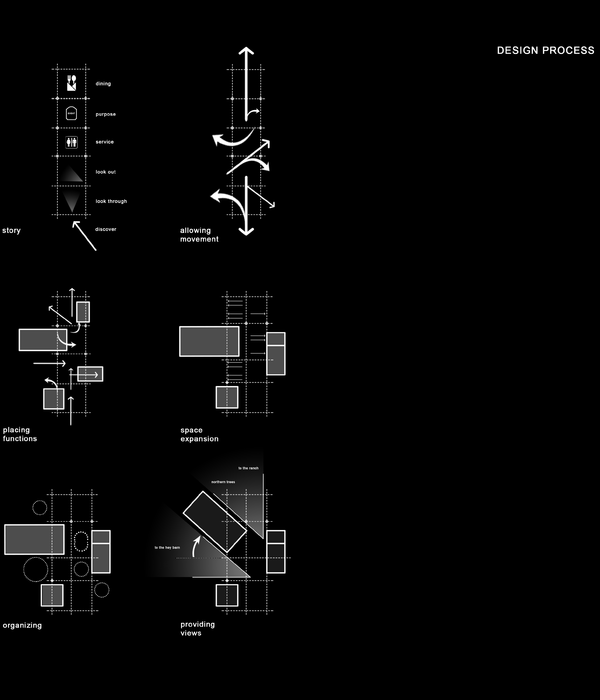'Infinity on Trial' is Julian Schnabel's debut exhibition with Blum & Poe and first solo show in Los Angeles in nearly a decade
“我想我们要找到我的线索,”朱利安·施纳贝尔解释说,他穿着紫色睡衣,穿着一件夹克,从他的盲人女子冲浪俱乐部与RVCA合作,在“审判无限”的预览中,他的首次展览是蓝色的。
因此,从1982年到2015年,施纳贝尔在第一家画廊组装了四幅油画,坚定地确立了他将(或制作)发现的物体、图像和绘画装置纳入画布的偏好;这不仅拓展了传统的绘画概念,也拓展了施纳贝尔对一切绘画的看法。这条隧道(一只蚂蚁在该国发电厂附近死亡)是1982年在胶合板上刷上薄薄的油漆制成的,胶合板被吹过,需要邦多修补。旁边是“胜利的边缘”(Edge of胜利场),这是1987年创作的一幅作品,由一名住在他的工作室里的艺术家送给施纳贝尔(Schnabel),由他的工作室里的一位艺术家给施纳贝尔(Schnabel)。这幅作品曾被安装在麦克·泰森(Mike Tyson)曾经训练过的格拉莫斯体育馆(GramosGym)。在这些作品的另一面是两张未命名的喷墨印花在聚酯上,其中包括档案壁纸图案,标本山羊,和扫地喷漆(从软管和气雾剂罐),这些结合了绘画姿态和拼贴-“浸渍表面”,如艺术家所说,以一种可能被认为是‘施纳贝利安’的方式。
Schnabel说:“我觉得走进这个房间看到这些照片是很令人惊讶的,但这个空间的伟大之处在于你有这么多的优势点。”他指出,你可以从画廊看到他1984年的“天鹅绒复活:阿尔伯特·芬尼遇见马尔科姆·洛瑞”-这是他当时被那些人批评的作品之一。他认为天鹅绒是一种花哨的材料,尽管它产生了灿烂的饱和颜色。“再生二世”也在展出,这是一幅1986年的油和火画,上面是从歌舞伎剧院买来的满是樱花的背景画,而他2015年对菲利普·西摩·霍夫曼的敬意-画在他去年在墨西哥买来的一张肮脏的塑料乐队封面上-以及一幅他1975年作品的灰泥-迈克尔·特蕾西的宗教画,笔触似乎是饱和的,新鲜的。表面,是在视线中的拳击地板和喷漆绘画从1987年和2014年。
施纳贝尔说:“这让我非常满意。”施纳贝尔自己在南画廊安装了自己的第一幅版画“病人和医生”。1978年夏天,施纳贝尔访问巴塞罗那时,为了模仿拉姆布拉斯酒店房间的壁橱和墙壁,施纳贝尔说,这些作品-他画了另一幅名为“时尚之死”(The Death of时尚)的画,但他指出,“我不认为时尚与艺术有任何关系”-从安东尼·高迪(Antoni Gaudí)的瓷砖工作台上拿出了一页。这篇文章的灵感来源于安东宁·阿托德关于梵高的文章“被社会自杀的人”。但夏贝尔承认,如果他看到了万斯教堂,他可能根本不会画出这幅画(画树木、躯干和柱子的线条)。亨利·马蒂斯(Henri Matisse)在那里设计了三幅白色陶瓷壁画,这些壁画都是他直接用黑色颜料在瓷砖上画的。在早期,他甚至用防水布给他们盖上防水布。
当人们问,“那是什么?”,我会说,“没什么。”我一次只展示一个,我不想让他们一次看到一个。杰夫只想展示其中一部作品的冲动,可以追溯到我小时候对我来说很有意义的事情。“关于如何看一幅画,有很多的概念,”施纳贝尔说。他承认,在马克斯的堪萨斯城和加里·斯蒂芬和大卫·迪亚奥度过了一个深夜之后。我以前经常和这些年长的人一起喝酒,我可能是麦克斯餐厅去年开业时最年轻的人。加里和大卫过来后,我说,“我有一幅画要给你们看”,他们看着那幅画,加里·斯蒂凡说的第一件事是,“那不是一幅画,那是一种解脱。”我说,“嗯,这可能不是你的解脱。”
在第三画廊,施纳贝尔在他2014年涂有树脂涂层的油肖像塔蒂亚娜·利索夫斯卡亚(Tatiana Lisovskaia)对面,安上了杰克(Jack The Bellboy),作为杜克萨·德阿尔巴(Duuka de Alba,II)和形状不规则的粉红和白色拼凑的布料屋顶。次年,他从一家墨西哥玩@@施纳贝尔说:“我做了一个担架来配合它的形状,我让一位女士把这件衣服缝在上面。我喜欢太阳把它漂白的方式。”“我并没有一个真正的等级概念之间的肖像,其中有一个历史叙事,和一个白色的标记,是用鲁斯特洛姆和白色喷雾器画在这个屋顶上。”我基本上可以把这和那个看作是一回事,但很明显,它们是不同的画意。
另一组画家的担忧-在美国很少见-是施纳贝尔在纸上的作品,其中一些作品在楼上的画廊里展出。除了世界各地的许多地图作品-包括对西摩·霍夫曼(Seymour Hoffman)的三次致敬,还有其他地图上写着“菲尔”(Phil)的红画-还有对迈克·凯利(Mike Kelley)的致敬,这是一幅棉球画,画的是十字画、笔记本纸和19世纪发现的玻璃上的喷绘画。(“我喜欢喷雾剂和图像之间的空间,”他注意到一处污迹,问画廊主任,“我们能把这些东西清理干净吗?”)
今年1月,在慕尼黑,一名打印机在自家后院制作了一系列紫色墨水和石膏系列作品,这些打印机在最近的山羊画中炸毁了档案壁纸上的细节。当被问及他使用这么多紫色(无论是历史还是最近)的动机时,他说有天主教色彩,但最终这是“人们为什么要做事情,如果他们给你一个撒谎的理由,这是完全不理性的”。为了说明他的观点,施纳贝尔以一系列有趣的轶事结束了他的旅行。
一年,我在纽约买了所有的紫色,所有的矿物紫罗兰。我并不是有意的,但这是一种有趣的颜色。当[商人] Gian Enzo Sperone过去看到紫色时,他会握住他的球,因为紫色代表死亡。这是意大利语。然后他习惯了,”他开玩笑说,补充说,在1982,“Gian Enzo对我说,”你为什么想成为一个变色龙?“这不是想做那件事,有时候你只是在做一些不适合别人做的事情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时刻。
A defined painterly language has pervaded his works on paper and canvas for the past four decades. Pictured: Untitled (Spray paint painting), 2014
As such, rather than focus on a single series of new works, Jeff Poe encouraged Schnabel to use his archive as a narrative device to bridge the gaps in his numerous stylistics shifts over the years. Pictured: Untitled, 2015
‘One year I bought all the purple, all the mineral violet, in New York City,’ says Schnabel, referring to his repeated use of the colour. ‘I didn’t mean to be such a pig about it, but it’s an interesting colour’
In Gallery One, Schnabel's 1984 work on velvet, Resurrection: Albert Finney Meets Malcolm Lowry, is on display – one of many criticised at the time by those who deemed velvet a gimmicky material, even though it produced brilliant saturated colors
The Blum & Poe exhibit includes four paintings from 1982 to 2015 that firmly establish Schnabel's predilection towards incorporating (or making) found objects, images, and pictorial devices into canvases. Pictured right: The Edge of Victory, 1987
keywords:Los Angeles exhibitions
关键词:洛杉矶展览
{{item.text_origin}}